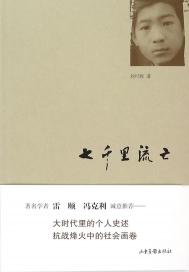1937年夏天。
一个非同寻常的夏天。7月7日,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个团,在北平卢沟桥抗击日寇,抗日战争爆发了。
济南有日本领事馆,馆内设有武官(特务机关)。日侨有数千人,他们办报纸,设公司,开商店,建医院,还开妓院。公司、商店收购中国土产,推销日货。多数商店都出售毒品,如海洛因、吗啡、“快上快”。战争爆发,这些日本人(济南人叫他们日本鬼子)都回国去了,朝鲜人也走,有走不脱的,被警察拘禁起来。在经五路纬一路西,路北一家店铺,我亲见警察带走三个“高丽棒子”。那三个人个头很高,手里各提着一个装着衣物的布袋,另带着一袋馒头,乖乖地被押走。他们的商店卖高丽人参,也卖毒品,在日寇卵翼下为虎作伥。
日寇飞机往往单架低飞盘旋在济南上空,恫吓济南市民,实际上震慑胆小鬼山东省政府主席、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。一架敌机投过一枚小炸弹,落在筐市街马路上,据说炸死一条狗,炸伤一个开茶馆的人。
二十九军是好样的,坚决抵抗,副军长佟麟阁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战死在北京南苑。三十八师从天津边打边撤,雨水大,河水泛滥,士兵蹚着没膝的水与日军作战,极其艰苦。
中央军的第十三军,本是调到晋绥堵截红军的,此时开到南口一带抗击日寇,第四师的罗芳珪团打得很顽强。但阎锡山的外甥、军长李服膺,率全军不战而失天镇、阳高……成为日寇的引路人,敞开了雁门诸塞。全国激愤,纷纷责难。阎锡山只好将他枪决,因为丢失的全是他土皇帝的地盘。刑前还训他一顿——也算是大义灭亲吧!另一“长腿将军”刘峙,在平汉线跑得更快——“日本飞机都赶不上他!”或因是蒋介石的亲信,不仅保住狗头,且重用依旧。
济南市街头一度蜂拥着过境的平津流亡学生,他们是从天津过海,由烟台、龙口到来的。据报纸报道,经过商谈,山东当局接待了他们,提供食宿。这些流亡者不仅以北平、天津的衣饰给济南带来了新街景,更以热情的抗日救亡宣传,给山东沉闷的政治空气以有力的冲击。
8月13日,日寇在上海挑衅。蒋介石把三个半机械化师调上最前线,八十七、八十八、三十六师三个师打得英勇,振奋人们的爱国心。中国空军在杭州基地出战、应战,打落敌机若干架,且数炸敌舰,改变了中国军民单纯挨空袭的状况。宝山姚子香营坚守不退,全部战死!谢晋元团,号称“八百壮士”,孤军固守四行仓库,打退日寇的多次进攻。所有这些战况、战绩,都为人们所称赞。
邻居乔振华初中毕业后,在反省院当狱卒。他说,政治犯都释放了。他们还劝他跟他们一起去闹革命。
韩复榘的军队在冀鲁边界的山东一边。日军到边界后停顿下来,不知在做什么鬼文章。省里的报纸还报道“四十一军过境扰民”,可见有省外部队到过山东。人们说韩复榘搜刮的民财都存到了日本银行,所以不敢同日本鬼子打仗。他有五师一旅,大兵个个吃得肥头大耳,但武器老旧,皆备有“大刀片”。
1928年的“五三惨案”,济南曾被日寇占领一年之多,兽兵烧杀淫掠,残暴已极,数千军民丧生……人们不会忘记那血与火的日子,谁还愿作第二茬亡国奴!
传说回族败类、五四运动期间镇压山东人民的马良[1]
准备迎接日本鬼子——这是半公开的,大概得到韩复榘的同意。
8月下旬,老人们说:夜静时,已听到北方传来的隐隐炮声,“像关大门似的”。
山东省立济南初级中学在隐隐的炮声中开学。
我因病休学一学期,家境困难,只到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就诊了一次,服药甚微。但几乎天天爬四里山、马鞍山,或去较远山野漫游……身体日健,准备秋季复学。
学校秋季开学前,我去教务处报了到。
清朝末年,废科举,办新式学校。山东省在杆石桥外东西大道北面的土岗上建起了山东最高学府——广厦宏伟、青瓦粉墙的大学堂。校门大约是按品级建造的,类似省布政使司衙门。学堂的中轴线上,进大门后为办公厅,向北依次三座两层大楼。大楼两侧是对称的教室,再侧为对称的学生宿舍。这些厅楼室舍间均连以长廊,既避强烈的阳光,又遮风雨,挡霜雪。其他部位为草地、花园、电厂、饭厅、浴室……是一所典型的棋盘式建筑群。学校的东南隅为学官官邸,高台、广厦。大门为城门式,上有雉堞。据西关回民老户赛培大爷说,学官因公出门,坐八抬大轿,非常气派。其他学校官员在街南另有宅院,也是青瓦、粉墙,超于普通居民之上。直鲁联军被驱走后,这里成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校舍。而后,改为山东省立高、初中两校,校舍一分为二。东部为初中,以学官官邸的大门为校门。
开学了。
礼堂里空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座位,显得很冷清。老师们坐在最前排。同学们见面很亲热,但又觉得有些陌生。战争,使大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。显然,远县的同学到校的不多,济南及附近各县的同学几乎全部到校了。
礼堂里不记得挂过孙中山像,更不用说蒋介石的了。也不记得挂过国旗,更不要说党旗了。开会时,从未唱过“三民主义……”谁应该讲话,谁就走上前去,站在讲桌后面讲。除非请外来的讲演者,也没有“主持人”。孙维岳(东生)校长当然先讲话。他四十岁左右,身材高大,隆鼻朗目,头微偏,有时颤动。他声音清亮,话语条理,开口便谈战争。
讲话大意:
战争可能打下去,日本鬼子或许不再采取蚕食政策,想一举灭亡我们中国,让我们当亡国奴。欧洲有十年战争、三十年战争、百年战争……这次抗战要打多久,很难说。唉唉,欧战还打了四年呢,中国还参了战。你们那时还没出生,我是经历了的。打仗,总会停停打打,打打停停……
大家必须读书,我们是教员,你们是学生。我们应当把你们培养成国家的人才,要弦歌不辍。读书也是抗战,也是爱国,也是救国。济南要是不能待,我带你们走,不做亡国奴!
胡维城(干卿、干青)老师第二个讲话。他是年逾五十的老人。他当过教务主任、事务主任,代理过校长。本学期是个“清”教员。他绰号“胡老干”,髭黑,体健。他说:
“听说日本鬼子占了天津,下令中国人都得弯着腰走路……”
他挺直了身子,拍拍胸膛大声说:
“我这副腰板就是弯不下去!”
两位老师的话真有气概,多么能打动少年们的心啊!他们不仅自己坚决不当亡国奴,还要带我们这一群少年人出走,把我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才。多么有信心!多么有远见!他们预见到战争不仅是持久的,而且终将会取得胜利。
每一个同学不能不一再思考他们的讲话,抉择今后应走的道路。我们三个年级的同学,个别年龄大者不过十八九岁,初入学的一年级小同学,大都才十二三岁,未来艰苦的流亡生活,将严酷地考验每一个出走者。
孙东生老师出身于成武县书香门第,父亲曾任东昌府学道。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,兼及老庄。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,曾撰写并出版过半部《中国文字学》(上),自序上写到“东生雅好文字学”,因而成为笑谈。他以中等学校国文教员起家,后来做校长,并成为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亲信。
他受过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熏陶,还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大会。何思源把原来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分为高、初中两校。大约是让两位校长做他的“交际员”,代他送往迎来那些政治、文化、宗教等方面的官僚、政客、学者、名流。这样就扩大了这位初中校长的接触面,自然受到不同思潮的影响。
他曾被山东省教育厅派往欧洲考察教育,到过南欧、西欧、北欧和苏联。在伦敦,他听过海德公园各派的政治演说,旁听过下院的辩论。他观看过德国纳粹的游行,访问过安徒生的故乡,参观过苏联的体育节……(他与邹韬奋同船到达列宁格勒,还在莫斯科巧遇王统照)。各国的教育概况、政治、文化等方面的见闻,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。他写的“通讯”,连载在一家报纸上。他过罗斯托夫时,正值中秋节,月色皎洁,思乡情发,曾有“今夜月团圆,故国是中秋。光明无限界,也应照中州”的诗句,可能还包含着其他的情愫。
他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“中学”,又接触到形形色色的“西学”,有的分辨过,有的也许不分辨,回国后形式上照说,照做,在济南初中试行。实际说不过是些皮毛,他不能也不敢更改国民政府教育上的老套。
他规定学校每日早晚升降国旗。定校色为“紫”,把一块长条紫布悬在国旗下每日升降,说那是校旗,但不久又拆掉。(定“紫”为校色或许与美术教员桑子中有关。李广田先生的散文《一个画家》即记的桑子中老师。老舍先生在济南时曾为桑子中老师画集作序。桑老师专攻西洋水彩,喜欢浓重的颜色,尤喜爱“紫”。他在大明湖铁公祠创办的“海岱美术馆”,窗帷全为紫色。)校色、校旗采用“紫”色的意义是什么?有一次,他说代表铁与血,那不成为俾斯麦的一套吗?反正,他以后未再解释过。上学期,学校还有了校歌,唱“我们是紫色的一群……我们是早晨的太阳,我们是迎日的朝云……”使我听了很新鲜。歌词作者是国文教师李广田,谱曲者为音乐教师瞿亚先。校徽是桑子中老师设计的,呈树叶形,底子也是紫色。学校参加省、市运动会的运动员全穿紫色背心。
他把童子军的领巾夏天改为领带,紫色(济南市的各初级中学都跟着学,如育英中学就打绿色领带)。童子军服的袖子夏天卷到胳膊肘以上,这违反了韩复榘的禁令,特别是女学生,幸而未受干涉。济南市在趵突泉建了自来水厂,他提倡喝自来水管子里的凉水。他说英国免费供中、小学生牛奶,每天早晨进校后即喝一瓶。济南虽有了五大牧场,但谁会免费供奶?学生能自己订奶的为数甚少。
他师法蔡元培“兼容并包”的精神,敢于请曾是共产党员的马克先任史地课,又安插另一曾是共产党员的张揆一在校养病,特为他设一门“卫生课”,得以教书有些收入。法院曾传讯他们,他代替他们到法院受审,并为之辩护。教员中不乏法西斯分子,也有托洛茨基主义者……有些是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,如训育主任、训育员、童子军教员之类。
因为兼任何思源的“交际员”,借交际之便,他请一些人到校讲演。如天主教的于斌、“新生活”的徐庆誉、“中国文化本位”的“领班”陶希圣、戏剧家熊佛西、水利专家张含英、宣扬美国文化的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、留英回来任山东省政府参议的徐子骏等等,都体现出他那“没有章法”的头脑,包罗万象。
他爱教员,因为自己是教员出身,弟兄中也有几个是执教鞭的。每年暑假总要去北平,跑北大、师大、清华,为延聘优秀师资做征询。教员中有患慢性病的,如魏绍谦(仲)老师,则让他减少些课时,继续任教,免得因病失业。
他爱学生,喜欢学生称他为老师,而不愿听“校长”二字。往届几个学生因放春假的事打了省督学,也打了他,砸坏了校产、校具。按校规只好开除。这些学生大都去北平继续上学。他有次去北平,还请他们几位便餐,不计前嫌。几位学生大约不好意思,没有赴约。又如学生胡腾驹(后改名胡可)画漫画讽刺教务主任丁用宾,张贴在布告栏。因临届毕业,为他办了个“转学育英中学”了事。
他是位“婆婆校长”,教务归丁履观(用宾)老师,事务有胡维城老师,部分时间不在校内,因为他兼着何思源虽无名义,却是事实上的“交际员”。
胡干青(卿)老师出身于济南近郊农家,毕业于优级师范。他原来在中等学校教数学,后来自学英文,达到口译“文绉绉”的程度。后来,就改教英文课。济南初中有“三卿先生”,即数学教员王荩卿、张绶卿和胡老师三人。他们教学认真,经验丰富,各有教授方法,富有独创性。学校在二门外走道旁给他们建立了塔形纪念碑,还为学生设立了“三卿先生奖学金”。胡老师冬季穿黑色棉袄、棉裤、棉大衣。夏天,同王、张二位老师一样,穿短夏布大褂。这种装束,与有些教员的西服、革履、呢大衣、呢帽和纺绸大褂,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我在济南初中读书以来,胡老师一直担任事务主任。两位事务员、一位会计、十几位工友是他得力的帮手。房舍虽老旧,但都整修得完整、洁净。他督工拆掉城堡式的校门,装修上铁棂子的大门,很有现代化的气象。他事必躬亲,有时爬墙上屋检查罅漏。他处处节俭,减少开支,尽量为学校储集资金。孙校长的开支大手大脚,常常受到他的节制。他处处为学生节省,做童子军服不用咔叽布而用土斜纹。学生食堂一度吃窝头,也是他赞许的。1935年下半年,我交了八元钱的书籍、服装等费,适爆发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,省里令学校“提前放假”,我交的费用退回了三元多。(山东的省立中等学校不缴学费、住宿费、水电费,也无其他杂费。)
胡老师爱学生,把可容五百人就餐的餐厅拾掇得干干净净。每星期开放浴室一次。每一排宿舍有一个工人管卫生,供应开水,代学生去校外购物。他企盼学生们健康成长,让工友在教室前种花,组成英文口号:
“Sunshining!”“Boysup!”
济南市有英、美、日、德等国的领事馆,馆内都竖有高高的旗杆,挂着米字、星条、红膏药等旗,以英国领事馆的旗杆最高。胡老师请来木工,制作了超过英国领事馆的全市最高的旗杆,树立在大操场上!
胡老师不畏权贵,敢作敢当。据说,某次陈立夫来到济南,在进德会向全市中等学校师生讲演。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党官电话通知去听。他当时代理校长,问道:“听讲演耽误上课,不去行不行?”党官“啪”地挂上了电话。他让学校照常上课,未去听。
我被编在22级1班,人数不少,几乎满员。课程一如既往:英、汉、算、史、地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公民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,还有童子军。
国文教员孟浦云老师,一口沂蒙土腔,讲课像老婆婆。他曾在《水星》发表过诗,《嘉树》(济南初中的文学期刊)上的《怀土篇序言》写得也朴实、耐读。代数是张绶青老师教,因为秃顶,常穿蓝布衫袍,讲课时右手上下“砍”动,早得“张和尚”的绰号。他的解题方法简便易作。公民教员闫子桂,本学期从私立齐光中学聘来,在课堂上讲“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”,使人觉得别有身手。他那有些矜持、傲慢、做作的姿态和声音,又使人觉得不舒服。
我与新同班很少接触,多与21级1班的老同班来往。张清洋买来《谈风》,在宿舍里朗读我写的《五三惨案回忆》。这是旧恨,却又来了新仇。大家万分痛恨日本鬼子!
战争影响着老师和同学。教师不像过去那样严格要求学生,不再布置很多的课外作业。同学们课外总在议论着战况,盼望中国军队打几个胜仗,遏止住日寇的疯狂进攻。然而,部队在节节败退,有的不战而逃,大家对抗战前途不能不有些悲观。
我是通校学生。一天中午,在赴校路上见墙上贴着“李公朴下午四时在青年会演讲”的公告。我告诉了李振泌等。啊!“七君子”之一,大家都急盼瞻仰他的风采,听他的抗日宏论,约定结伴去青年会。下了第二节课,时间已近四时,大家便急步出校,一路小跑,向青年会奔去。
会场设在室内篮球场,听众已爆满。我们硬挤了进去,几乎人贴人地立定了脚跟。只见屋西头中间放着一个木箱。不一会,一位着西装的青年会工作人员,陪着李公朴走到木箱边。李公朴中等身材,浓眉大眼,面色红润,颌下满把短髯。他穿一件“卡克”,马裤,足蹬短靴。我们早已在报刊上见过他的照片,觉得并不陌生。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一作介绍,会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李公朴满面笑容地站在木箱上,向大家挥手致意,开门见山便谈“抗战”,声如洪钟,面容随讲演内容变化着,手势打得沉着有力。
他说刚从北平、保定前线绕道来到山东。他激情地谈南口守军如何英勇抗击日寇——轻伤不下火线,重伤者因救护人员缺乏,又少担架,只好滚爬着退到第二线……
他着重说这是全民抗战,要支援前线,打退日本鬼子的进攻……
全场肃然,大家随着他的情感,洪钟般的话语,心胸激荡,热血沸腾。
最后,他话锋一转,说山东当局对抗战态度暧昧,不明朗,是与全国抗战热情不相称的。“我准备向当局痛陈利害,晓以大义,赶快动员起来,跟上全民抗战的步伐!”
一谈到对山东当局的不满,掌声便轰鸣起来。
听了李公朴的讲演,我们兴奋了好几天。他说出了大家想对山东当局说的话。
听说城里济南师范有讲演会、报告会,我们就去看看。这所学校并未开学上课,成了群众集会结社的地方。(根据中共党史资料,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曾借此约人见面。)
杜若君在讲什么国际形势,一张苍白的脸,声音低,口才也不算好,听众不多。他常在《世界知识》上发表国际问题的文章,自学成才——曲阜师范的图书管理员。
张友渔[2]
、齐燕铭[3]
在行政人员训练班任教,又听说那里有什么集会,但去后什么也没见到。
市立图书馆仍在开放,我照常在课外活动时间及假日去那里阅览书报——我的第二学校。那位老管理员仍在认真上班,有时听到炮声,我们相对苦笑。
某天,孙校长请来一位演讲者,大家都去礼堂听。我没听清他介绍讲演者的官阶、名讳,只见那人约中年,个头不矮,笔挺的中山装,金边眼镜。他是南方人,操着国语,很简洁,顿挫有力。他说天皇裕仁如何如何,大约是在耻笑。谈到战争前途,他说对敌作战如“秋风之扫枯叶……”
听完讲演,才知道他是大人物—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方治。他的“秋风之扫枯叶”,把日寇说得不堪一击,大家很怀疑。蒋介石或许有什么坚甲利兵吧?二百个师啊,不能都同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一样是些“吃饱蹲”吧?不过这种夸大的词句,令人难以相信。
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,歼灭敌阪垣师团一部,缴获大量枪、炮、弹药、服装……大快人心!第八路军真是一支神奇的部队!该部又在阳明堡烧毁敌机二十四架,配合了忻口大战,又一次大快人心!真是神兵!
忻口大战,中国军队打得英勇、顽强,坚守阵地,誓不撤退。杂牌军军长郝梦龄及其师、旅长亲到最前线督战,壮烈殉国了。
日寇侵占了桑园,进入山东境地。不久,德州沦陷了。
省立德县初中和教会博文中学逃来济南几十个师生,加入了我们的学校。
据说第三路军展书堂师曾在津浦铁路正面抵抗。我小学时的同学侯连生、白书田战死了。他们是篮球场上、乒乓球台上的好手。他们从这所小学毕业,又去上另一所小学,不想升中学或考不上好中学。在省立第二实验小学毕业后没再读书,后来去当了兵。传说他们约合同伍,拜了把兄弟,围成一圈相对磕了头,决定爬日寇的坦克,揭开盖子往里塞手榴弹——都为国捐躯了!
第三路军曹福林部在陵县凤凰店与日寇相持,打了几仗。报纸上曾报道那几次战斗。又传说韩复榘曾到前线,适值日寇飞机投弹,大炮猛轰,吓得急忙逃跑。他本不会骑摩托车,竟然骑上跑起来。大约是他的喽啰瞎编的,意思是“韩主席福大”!
济南终于失去了平静。内地人及本省家在乡下的人们,已陆续迁走。几条繁华的大街上行人稀少。市里没有驻军,警察在维持治安和交通。
[1]
马良(1875—1947),河北清苑人,回族,出身北洋新军,曾在山东任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、济南镇守使等。济南沦陷后被日本人任为山东省省长兼保安总司令,后加入汪伪政府。1946年在济南被捕,以汉奸罪下狱,1947年病死狱中。
[2]
张友渔(1898—1992),山西灵石县人。1927年加入中共。抗战前曾任北平《世界日报》总主笔,创办《时代文化》,任燕京大学等高校教授。七七事变后,在济南、开封等地,先后任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,中共豫鲁联络局书记,1943年后在重庆任《新华日报》代总编。抗战胜利后参加国共谈判。1949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、北京市副市长等职。19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。
[3]
齐燕铭(1907—1978),北京人,蒙古族。抗战前在北平中国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。主编《时代文化》杂志,“一二·九”运动领导人之一。1938年加入中共。任鲁西北《抗战日报》主编等。1940年去延安。1943年主持创作评剧《逼上梁山》,导演并饰林冲一角,得到毛泽东好评。1949年后历任中央政府办公厅主任,政务院副秘书长,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、总理办公室主任,文化部党组书记、济南市副市长、全国政协秘书长。